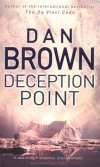防火牆
出版:麥田(2002/8)
作者: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作者簡介(取自書耳作者簡介)
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1930年8月1日生於法國庇里牛斯山—大西洋省的東洱市(Denguin)。先後在波城(Pau)中學、大路易中學、巴黎大學文學院及高等師範學院受教,取得哲學教師資格的學銜。1955年任教於慕蘭高中(lycée de Moulins),1958年到1960年任教於阿爾及爾大學文學院,1961年到1964年在里耳(Lille)大學任職。自1964年起任教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1981年正式成為法國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社會學教授。他同時也任高等社會科學院主任、歐洲社會學中心主任,並主編1975年創刊的《社會科學研究學報》(Actes de la recherché en sciences socials, ARSS)。著有《繼承人》、《再生產》、《區別》、《實踐感官》、《實踐理性》、《世界的悲慘》等書。2002年1月23日辭世。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
在討論布赫迪厄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之前,先簡單介紹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但是要知道什麼是「新自由主義」,就必須對「自由主義」的發展有初淺的認識。
一般公認,「自由主義」的創始者為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至於「自由主義」為何會出現在英國?為何會由洛克所提出?這是有其相當複雜的歷史與思想的背景,這裡只簡單介紹一下洛克的思想概要。洛克認為人都是生而自由的、平等的、獨立的,因此要了解人,必須就個體的人做觀察,而非從整體的人來了解。道德上的善惡,就個人而言,不過就是經驗上的樂與苦而已。每個人的經驗的不相同,所以善對每個人而言都是不相同的。這種以個人的經驗為道德與知識的哲學基礎,正是所謂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又稱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
「自由主義」的發展到了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便分成兩派:一是原先以英國「個人主義」為發展背景的「經驗哲學」,這派代表人物除了洛克外,還包括柏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休姆(David Hume,1711-1766);一為受到歐陸浪漫主義影響的「唯心主義」(Idealism),代表人物包括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前者的發展到了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提出「看不見的手」之後,成為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開端;後者到了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因資本主義流弊與歐洲社會主義悠久傳統,結合當時科學研究方法而成為「馬克思主義」(Marxism)。
「資本主義」發展到後來,其追隨信徒如邊沁(Jereme Bentham,1748-1832)、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1773-1836)與約翰‧米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父子等,而提出了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善」這種後來稱做「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信條。其中因約翰‧米爾曾與其妻子海麗‧泰勒(Harriet Taylor)合著一本諸名的《論自由》(Easy on Liberty),而被尊稱為「自由主義」之父1。本書中約翰‧米爾為思想與言論的自由提出強有力的辯護,並且建議對國家干預人民生活的權力設限。這種說法其實仍是溯自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的「管得最好的國家最好」此一論點,這是因為傳統「資本主義」受到洛克契約論的影響,認為國家不過是人民之間為了避免「自然狀態」的慘狀,所不得不放棄自己一部份自然權利而定約所成立者,而國家的義務即在於維護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這些自然權利,如果國家未能實踐此義務或超出契約中和人民所約定的事項,代表國家無法履行契約或破壞約定,因此人民有權推翻國家另訂新約。因此,「資本主義」一開始也認為國家管得越少越好,但是到了20世紀時的30年代,發生了經濟大恐慌,當時為了刺激景氣成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理論因應而生。
1. 很巧妙的,海麗‧泰勒的名字與對自由主義的貢獻被「刻意的」忽視了。這是一些女性主義對自由主義深不以為然的緣由。
凱因斯理論的一大特點,就是利用國家的力量,以增加政府支出、調降利率、與減稅等政策措施刺激市場需求的有效提升。當時運用凱因斯理論最成功的國家,包括二次大戰前的德國與美國羅斯福「新政」。後來因為擁護凱因斯理論的政策支持者,為有別於傳統「國家管得越少越好」的政策主張,而將自己稱為「自由派」,並將傳統理論的支持者稱為「保守派」。然而,凱因斯理論並非毫無問題。由於政府無限制的支出,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惡化,而由政府所介入的各項公共建設與事業,也因為缺少競爭因素而導致效率不彰、浪費與負債等。為了解這些問題,並進而提出解決方法,經濟學轉而訴求傳統理論中的「市場競爭」法則,再次提出「國家管得越少越好」這種論點。不過,這次傳統理論的「再生」,有別於傳統理論之處,在於其能提出一套結構嚴謹的數理論證方法,證明「市場法則」的有效性,以推翻國家力量介入市場的理由論據。這類的政策主張包括英國柴契爾夫人當政時的柴契爾主義,與美國雷根總統時代的「供給面經濟學」等,其主要的政策論點包括:國營事業民營化、降低營業稅、使用者付費等。
再次的,為有別於傳統理論,新興的傳統理論將自己稱做「新自由主義」,而把傳統理論稱為「古典理論」。「新自由主義」支持者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派」,於是將主張由國家力量主導市場運作的支持者稱為「保守派」2。「新自由主義」的幾個重要理論學派,包括:貨幣理論(Monetary Theory)、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Theory)、財產權理論(Property Theory)、與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等。這些學派與理論的重要領導者,如傅立曼(Milton Friedman)、貝克(Gary Becker)、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人,更是80到90年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常客。這些人的論點,在90年代末至今,也成為台灣政經學界的顯學。
回過頭來看,左派社會主義思想自蘇聯解體之後,也非完全停滯不進。接著就來看這本反「新自由主義」大作(其實只是一本小書),《防火牆(contre-feux)—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裡面對「新自由主義」內所隱含的保守革命大加噠伐。
2. 這也是西方「自由派」與「保守派」有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的原因。在觀察西方媒體或學界主張時所指稱的「自由派」或「保守派」,必須仔細的釐清其真正的指射對象為何者。
防火牆(contre-feux)—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在《防火牆》一書中,利用在各地所發表的各篇短文與演講,提出他對「新自由主義」的嚴厲批判。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其實正是傳統那種以剝削弱勢族群為尚的資本主義的復辟。這次,資本主義有了科學的數理方法為武器,加上無知的傳播媒體、記者、與「媒體型的知識份子」3推波助瀾,漸漸危及社會主義運動經過多年鬥爭所獲得的文化基礎。本書雖分做多篇短文,但大致可分成四個主題:「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因、「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問題、對抗「新自由主義」運動、與如何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3. 「媒體型的知識份子」是布赫迪厄對電視媒體觀察與批判所提出的一個現象,其所指者即為那些在媒體主持人(包括記者、電視主持人等)所限定的議題、時間內能夠侃侃而談,卻又言之無物,不斷反覆複誦大眾都已知曉言論的那些「社會菁英」。
為何「新自由主義」會受到歡迎?
布赫迪厄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主要原因,一是「新自由主義」是一個「自我實現的神話」,一是「知識份子的墮落」。
韋伯(Max Weber)曾經說過,統治者永遠都需要合理化他們特權的一套神話,一套可以從理論上替他們特權辯護的社會正統論。其中以個人能力(天賦異稟)做為區別彼此,正是這套統治者及其他人所接受之社會正統論的核心。
這種以「回歸個人主義」的論點,正是一種自我實踐的預言。回歸個人,讓我們可以「譴責受害者」。因為受害者要為自己的不幸負責,也讓我們可以向受害者宣傳「自求多福」。於是,企業裁員美其名為「瘦身」,而被裁掉的員工則普遍視為「能力不足」者,這一切都是在要減輕企業負擔的幌子下進行的。其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正好提供一個為其特權辯護的最佳工具。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除了幾個例外)一個重視純粹數學方法的抽象學科,藉著一種狹隘又嚴格的理性概念(即個人理性)之名,計算出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存在條件。這種毫無理由依據的將經濟與社會一分為二,並提出其政策主張,正是造成所有政策失敗的根源,因為這種政策只知道要維護「經濟的穩定及秩序」,而忽視因此而付出的社會成本。但是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支持力量來自社會上的利益代表者,包括股東、金融操作者、企業經營者、保守政治人物、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社會民主黨人士、財經高官、以及那些不必承受任何風險的人。他們所代表的這股政治經濟力量,傾向於擴大經濟及社會的分裂,藉此在現實社會中以建構維繫其利益基礎的經濟理論。
知識分子雖然擁有文化資本可與統治者相抗衡,知識分子的義務正如哲學家,會去質疑那些理所當然的自明之理,那些是不管自己或他人看起來都有問題的自明之理。但是為什麼知識分子會從積極參與者,轉變成放任不管呢?一部份是因為知識分子雖然是統治者當中的被統治者,但他們還是屬於統治者的那一群4。另外,就是那些自以為懂得一點經濟學皮毛,就自認為可以去宣揚那些不當引用的經濟學字眼的政治人物、記者,和泛泛之輩的推波助瀾,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能散佈到經濟圈以外。這種一點一滴的灌輸,可以產生很深刻的效果。也因此,到最後「新自由主義」思想變得像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
4. 這必須從社會學中的階層、階級、宰制等觀念來想像。
「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問題
首先,「新自由主義」將破壞福利國家的哲學基礎。福利國家建立過程中所爭取到的各項社會權益,例如像工作權、社會保險等,都是經過無數次多少男男女女為此受苦及奮戰所獲致的成就,因此這些社會權益都是珍貴的人類文化成果,尤其可貴者,這些文化成果不是存在於博物館、圖書館或學院裡,而是活生生的在人們生活裡產生作用,引導著人們每一天的存在。
這些文明所累積的成果,需要的是普及化與世界化,擴散到所有的領域。但是「新自由主義」卻企圖從經濟上及社會上,以「全球化」或以發展較落後的國家的競爭為藉口,去質疑這些成果。「新自由主義」的意圖,就是要瓦解社會權益。其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國家的左手」覺得「國家的右手」5不再知道,或再也不想知道「國家的左手」到底在做什麼。總之,就是不想再付出代價。造成許多社會工作者絕望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家從許多屬於其管轄負責的社會領域中退出,或正在退出:例如國宅、公共電視及廣播、國立學校、國立醫院等。
5. 「國家的左手」是由所有社會工作者,如社工人員、輔導人員、基層行政人員、以及學校教師等所構成的;換言之,即為國家裡所有需要大量開銷的政府部門。「國家的右手」,則是由法國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的菁英所充斥的財政部、公民營銀行及部長辦公室所構成者。
其次,「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方面所造成的危機,則是出現對公共事務的漠不關心與「反國會主義」。這正充分反映出人民對於國家作為公共利益負責人的絕望心態。布赫迪厄指出,當人民對國家和公共福利進入信心危機的時候,可以看到兩樣東西的大放異彩:在領導者那裡,是貪污腐敗,這和對公共事務的漠視有關;在被統治者那裡,則是個人的宗教狂,因為他們對於訴諸現世,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最後,在社會上則形成到處「工作不穩定」的現象。「工作不穩定」現象影響所及不僅是工作者的心理層面,更影響了社會與經濟層面。布赫迪厄發現,如今工作到處都是不穩定的。不只是在私部門裡,在公部門裡也是,有越來越多臨時代理的工作。工作不穩定對當事人影響巨大,未來變得不確定,使之無法做理性的預期,生存的結構性破壞,包括時間結構的被剝奪、人際關係的惡化,然後是與時間空間關係的被拆解。
這種不確定感會一直在那裡,無時無刻的存在每個人腦海裡。也存在於意識與無意識之中。因為有一大群文憑所造成的後備軍,讓每個有工作的人強烈感覺到他個人的可替代性。他之所以能有工作,是一種特權,一種脆弱而且受到威脅的特權。客觀的不安全感形成一種普遍化的主觀不安全感。這不只是影響到所有的工作者,甚至也可以影響到那些沒有(或還沒有)直接受到打擊的人。這種「集體不安全感心態」,是士氣低落及社會動員瓦解的根源,更是造成人們之間「搶工作」現象原因。這種比企業間的競爭更為野蠻的搶工作現象,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相互鬥爭的根源,使得團結互助的價值及人情味都破壞殆盡,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
工作的不穩定除了直接影響到當事人,間接地也影響及其他人,不只是因為它所引起的恐懼,而且還因為有系統地利用所謂的不穩定化(工作臨時化)策略來製造恐懼。例如所謂的「彈性化」措施(包括工時、工資等),就是利用塑造一種不安全感的狀態來從中獲利,而彈性化又同時強化這種不安全感。它壓低成本,而成本要壓低,這就要使工作者永遠處於一種會失去工作的危機中。
6. 作者認為「彈性化」措施背後,不只有經濟動機,還有政治動機。
如此一來,工作的不穩定現象被納入一種新形式的宰制模式中。這種宰制模式,是建基在不安全感的普遍化及永久化之上,目的在使工作者變得順服,並且接受剝削。此即所謂的「彈性剝削」(flexploitation)概念。這個概念,提到不安全感的理性管理,特別是透過生產空間的操縱,在社會權益最多、工會最有組織的國家(這和一國之領土及國家歷史有關)的工作者,和社會權益上較落後國家之工作者之間,製造競爭。並且藉著表面中立的機制(如我們的勞委會),擊破抵抗的力量,獲得屈服和順從。工作不穩定所造成的屈服態度,是成功剝削的條件,其所靠的基礎,是為數越來越多的不工作者,和為數越來越少的工作者(但其工作分量也越來越重)之間的劃分。
這種新興的優勝劣敗制度,在不安全感、受苦及緊張狀態之中,找到工作者對工作及企業臣服的原動力。其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運作,主要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因為有「工作不安全感」的慣習;其次,則是在各個工作階層(甚至包括最高階層的管理幹部階層)中,都存在著有「一大群被工作不穩定及長期失業威脅所馴化的後備勞動力」。這兩者一起造成工作不穩定化的慣習。這個由「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經濟秩序(高舉個人自由)的最終基礎,其實正是失業、工作不穩定及害怕解雇之威脅所構成的「結構性暴力」。職業階層,到越來越近的整個社會階層,似乎是建基在一種由「能力」或(更糟糕的)「智力」來決定的層級上。
偉大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建立起的烏托邦,立即可見的效果是:經濟上最先進的社會裡,有越來越多的人飽受痛苦和不幸,貧富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電影、出版品等等自主的文化生產領域也因為越來越商業化而逐漸消逝。而能夠阻止這一惡性循環的集體機制(「公共」概念的普遍價值的看護者的「國家」)也受到破壞。在國家裡,在企業裡,優勝劣敗的觀念大行其道,加上對贏家的崇拜,人與人之間無所不爭,無所不鬥,犬儒成為所有行為的規範。
對抗「新自由主義」的運動
布赫迪厄在本書中所寫的短文,有許多是針對當時法國發生許多社會運動時而寫。收錄在本書中者,主要有:1995年10月17日巴黎火車爆炸案、1995年12月法國大罷工、1998年1月17日法國失業者佔領高等師範學院、以及他對「全球化」的批判。
巴黎火車爆炸案
1995年10月17日星期二,一輛巴黎區間火車的第二節車廂發生一起爆炸案。當時駕駛這列火車的一名鐵路員工,非常冷靜地疏散乘客之後,提醒大家不要把罪怪在阿爾及利亞社區的頭上。他淡淡的說,阿爾及利亞裔也只不過是一些「像我們一樣的人」罷了。
嚴格而言,本篇文章並非是自發性的對抗「新自由主義」思想運動,但是布赫迪厄卻因為此事件表達出他對法國內部存在的種族問題的看法。布赫迪厄特別稱許這位鐵路員工所說的這段話,他認為這段話正好戳穿一些法國政客與無知的傳播媒體,企圖將政治社會問題簡化的歸咎給法國境內的少數族裔(特別是阿爾及利亞族裔問題)6。鐵路員工的這段話,鼓勵我們更堅決地對抗那些只想便宜行事,企圖扭曲複雜的歷史事實,把歷史簡化成簡單而令人心安的善惡二元論的那些人。而這種二元論觀點,在電視媒體上卻已構成常態模式,只是簡單地表態贊成或反對一個想法、一個價值、一個人、一個制度或一個狀況,而無能於從事實上去分析它,多角度地來看它到底是什麼。
6. 1991年12月26日,阿爾及利亞舉行三十年來的第一次選舉,長期從事社會工作的宗教組織救世伊斯蘭陣線,在430個席次中獲得188席,贏得第一輪的選舉,卻被當時執政的軍政府以該陣線將要進行像伊朗激進宗教革命為由,在1992年1月11日禁止了第二輪選舉。這個選舉無效的宣告,還得到了原殖民宗主國法國的同意。從此,軍政府和宗教組織間結下不解之仇,以極端恐怖主義的瘋狂屠殺,經常出現在阿爾及利亞各地。
鐵路員工的這段話,也證明了人民有能力可以抵擋大眾媒體的語言暴力。在這個案例中,只有嚴謹的狀況分析及制度分析,才是對抗偏見和善惡二元論最有效的良藥。
1995年法國大罷工7
1995年12月因為右派政府所提出的社會改革方案,法國運輸工人發起一場為時近一個月的罷工運動。這篇正是布赫迪厄在罷工期間,為支持鐵路工人們所做的發言。
7. 1995年右派總理朱沛(Juppé)執政,針對繁冗的行政及整個社會福利系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面對歐盟有關財政赤字的壓力,政府宣布要將國家機器現代化,改革保險制度,限制工人領取退休金資格,特別是提高國鐵工人的退休年齡,延長工作時間等。11月11日,朱沛在國會提出改革方案,卻遭到公營部門和運輸工人自24日起發動罷工。近一個月的大眾運輸系統罷工,癱瘓了整個巴黎。朱沛拒絕工會的「談判」要求,直到聖誕節前夕社會高峰會議落幕。這個對抗當權者的社會運動,雖然促使朱沛下台,但是後來執政的左派喬斯潘政府卻沿襲不少朱沛的改革方案。
布赫迪厄認為這次運動,反映了法國當時社會上的階級對立問題。由當時執政總理朱沛的言論中可已發現,執政者刻意將社會劃分成「開明的菁英」和「衝動的人民」(及其代表)。這種言論其實是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的典型反動思想,只是今天它換上了一種新的面貌。這些新起的國家貴族,是藉由文憑及科學權威(特別是經濟學的)獲取自身信仰與言論的合法性。對這些統治新貴而言,他們堅決的認定理性和現代、運動和改革,都是站在當權者、部會首長、老闆或「專家」這邊的;至於人民、工會及批判的知識份子,都是不理性和落伍,遲鈍和保守的。這些新興國家貴族,鼓吹國家的終結及市場邏輯的全權宰制(用消費者取代公民)。他們的作法掠奪了國家機能,他們把公共財變成私有財,公共事務變成囊中物。
這次運動,代表的是民主對技術官僚的反攻,人民必須和專家專制做個了結。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這類的專家,強制我們接受新怪獸(財經市場)的判決,不願做雙方的協商,只想單方向的「說明」。我們必須打破「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所宣傳的歷史必然性,我們必須要創造集體政治運作的新形式,使之能把各種必要性,特別是經濟必要性(這可以是專家的工作)列入考量,以便克服甚至瓦解這些必要性。首先是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學者等,由他們幫忙打破技術官僚對傳播工具的壟斷。其次,從科學和經濟這兩處(「新自由主義」的強勢之處)著手,藉由反對他們那種抽象而片段的知識,以凸顯出一個較有人性與叫符合人所面臨現實的知識。
1998年失業者運動
1998年1月17日,一群法國失業者佔領高等師範學院時,布赫迪厄認為這個運動最特殊之處在於其最先爭取到的,就是運動本身的存在。這個運動使失業者及所有工作不穩定者(其數目每天還是不斷在增加)脫離隱形、孤立、沈沒的狀態,也就是脫離不存在的狀態。藉著重見天日,這些失業者使所有像他們一樣因失業而遭遺忘及活在羞辱中的男男女女,重新存在,重新獲得某些尊嚴。這個運動也凸顯出,現今,解雇的威脅仍存在所有階層中。工作的不穩定使得宰制及剝削可以得逞,無論是公營還是私營部門裡,整個職場都受其影響。
法國失業者運動的影響所及,在呼籲歐洲所有的失業者及工作不穩定者,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的顛覆性理念,這一理念可以成為鬥爭的工具,而每個國家的運動都可以運用之。這個運動中的失業者要提醒所有的工作者,他們和失業者其實是同夥的。失業者的出現,其實正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後果。唯有進行一場超越各國之內工作者與非工作者之分,以及超越國與國間的所有工作者和非工作者之分的動員,或許才能對抗那個藉失業者使工作者(一個擁有不確定性「特權」的不穩定工作者)乖乖閉嘴的政策。
對全球化問題的批判
布赫迪厄認為「全球化」只是一個迷思,一個強勢的言論,一個力量的概念,一個擁有社會力及讓人信仰的概念,是用來是對抗福利國家中社會權益的主要武器。「全球化」運動背後真正推動的是保守革命,倚靠的是進步、理性及科學(指的是經濟學)以合理化其復辟,並且把真正進步的思想和行動貼上過時的標籤。因此,歸根結柢而言,「全球化」只不過是一個為保守者辯解的迷思。
舉例言之,金融市場的全球化正逐漸實現。藉著減低各國內司法的控管,與現代溝通管道的改善(使得溝通成本下降),我們逐漸走向一個統一的金融市場。這個金融市場是由某些經濟體所控制的,也就是那些最有錢的國家,特別是那些國幣被拿來當作國際準備貨幣的國家,他們因此可以在金融市場裡擁有更大的自由度。金融市場做為一個行動場域,於其中,統治者(特別是美國)所佔據的位置使他們可以決定此場域中大部分的遊戲規則。簡言之,全球化並不是一種各國金融市場均質化的過程,反而是少數幾個宰制國家將其影響力擴張到所有國家金融市場裡的過程。
如何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認為可以從思想基礎、社會動員、知識份子責任、與建立跨國性組織來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在思想基礎方面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新自由主義」言論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散播出去的?經過對「新自由主義」論點的分析,了解其生產及灌輸的機制,才能抵抗「新自由主義」的臆斷。要使一個錯誤的思想成為自知之明,本來就需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不斷的製造這些逐漸成為所謂明顯事實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儘管這些想法一開始是反潮流而行)。以英國柴契爾主義為例,柴契爾主義不是柴契爾夫人時代才開始的,老早就有一群又一群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在報紙上擁有影響力的那些人)在為柴契爾主義鋪路。
其次,在面對這些機制時,我們該怎麼辦?首先,要去思考「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暗含的侷限性。「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評估一個政策的成本時,並不考慮我們所謂的社會成本。像解雇、苦難、疾病、自殺、酗酒、吸毒、家庭暴力等等,到底花了社會多少成本?它們之所以成本昂貴,不只是金錢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痛苦)。其次,即便是經過精確的成本效益分析,任何經濟政策也不會是省錢的與符合經濟效益。生命財產上的不安全感、治安上的花費等,都也要納入考量。因此,必須徹底質疑把一切(不管是生產,還是正義或健康,成本還是獲利)都個人化的經濟觀點,這種經濟觀點忘記了效率(在其狹隘而抽象的定義下,變成只是金錢上的贏利)取決於目標。必須先確定目標才能衡量效率,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忘記了原先的目標。
最後,面對權威效果,只能用另一個權威效果來對抗它。今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主流意識型態的作用,是靠著對純粹抽象數學的運用,而找到一個有力的武器。此一意識型態,為反動的保守主義思想穿上了純粹理性的外衣,所以要對抗它,同樣地也必須要用理性、論證、反駁、證明其謬誤。總之,就是用科學的方法來推翻它。我們必須創造一個象徵行動的新模式。因為任何社會法則或經濟法則,只能在任其而為之時,才會發生作用。我們的目標不只是要創新回答的內容,而且要創新回答的方式,將抗議及動員工作的組織方式進行創新。
在社會動員方面
要反抗「新自由主義」政治體制的政治鬥爭是可能的。首先,必須鼓勵被剝削的受害者(目前的或潛在的)一起對抗工作不穩定的破壞性效果,以慈善或慈善義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生活、相互扶持、維持尊嚴、抗拒自我形象的惡化及抗拒疏離。同時,因為不穩定化政策的效果是作用在國際這個層次之上,所以也要鼓勵他們「在國際層次」上去動員,才能戰勝這個不穩定化政策,使這個政策想在各國的工作者之間所製造的競爭,無以為繼。
其次,結合民間與政府部門的力量,以抵抗「國家的退化」,也就是說防止國家退化成刑罰的國家,或者說變成只會鎮壓,而犧牲其他社會功能(教育、健康、救濟等)的國家。社會運動可以從處理社會問題的政府部會,與協助長期失業的政策負責人中,獲得有力的支持。他們會擔心社會擬聚力的斷裂及失業問題,並考慮到因為崇拜生產力及獲利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忽視的社會痛苦成本。
最後,要用文化和理論的武器來對抗「新自由主義」。保守革命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招牌,因此看起來很科學,而且是個有行動能力的理論。相比之下,社會運動落後了好幾個象徵革命,因為社會運動的敵人懂得利用政治公關顧問、媒體顧問來包裝自己。許多社會運動理論在實踐上及理論上所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忘了去考量理論的有效性(行動能力),我們不應該再犯這個錯誤。和我們交手的對手,既然懂得用理論來武裝自己,所以我們要用文化和理論的武器來對抗之。
在知識份子責任方面
所謂的知識分子,是面對政權仍保其自由,敢於批評成見,瓦解簡單的二分法,並且重建問題複雜性的人。知識分子最適合的,就是去對抗媒體洗腦的工作。因此,必須勇於護衛知識份子批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批判所謂的意見專家所散播的臆斷(先入為主的意見)。沒有真正的批判力來制衡,就沒有真正的民主,知識份子正是最重要的批判力之一。
另外,布赫迪厄也希望作家、藝術家、哲學家及學者,都能在他們各自專業的公共領域上發出聲音。如果知識運作的邏輯(推論及駁斥的邏輯)能延伸到公共領域,則所有人都會是贏家。如今,反倒是政治的邏輯(抹黑、口水戰、喊口號、亂貼標籤)延伸到知識圈裡。
在建立跨國性組織方面
必須建立一個真正以國際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組織,使其能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在這樣的觀點之下,需要的是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而這一工作就落在工會組織身上。但是建立新的國際主義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除了傳統國際主義因屈服於蘇聯專制而名譽掃地外,就是工會結構的國家化問題(工會不只是和國家結合,甚至是國家組成的一部份),以及各國工會結構因為不同的歷史傳統而分道揚鑣。
那麼如何在工會層次、學術層次及民眾層次上,去創造一個新的國際主義組織呢?首先在於群眾的動員,尤其需要知識分子的涉入。因為有一部份的社會運動瓦解,是導因於傳播媒體不斷地「宣傳」所造成的士氣渙散,而這些「宣傳」是用讓人不覺得是宣傳的方式來潛移默化。其次,在這個國際動員之中,需要把重心放在理念的鬥爭上,特別是去批評統治當局及其思想打手所不斷製造及宣傳的再現(利用誤導的統計數字,及有關應美國家充分就業的神話)。
而在這些集體、團體組織、工會、政黨之中,必須賦予國家,最好是超國家,也就是歐洲國一個特殊的位置。因為只有國家力量,才能有效地控制及強制在金融市場上的獲利;只有國家力量,才能阻止金融市場對勞動市場所施行的破壞性行動,並且能夠在工會的協助之下,建構及護衛「公共利益」。所以在現行國際組織中,我們雖然反對建基在單一貨幣的歐洲整合,但卻一點也不反對歐洲的政治整合。正好相反,我們反而要呼籲建構一個能控制歐洲銀行的歐洲國,這個歐洲國要能預測並控制歐洲共同體之社會功能。簡而言之,相對於破壞社會權益的金融歐洲,必須提出一個社會福利的歐洲,使其建基在歐洲各國勞動者的結盟上,以便抵銷每個國家的勞動者(特別是透過社會傾銷)所加諸在其他國家勞動者身上的威脅。
 書名:A Feast for Crows (A Song of Ice and Fire, Book 4)
書名:A Feast for Crows (A Song of Ice and Fire, Book 4)